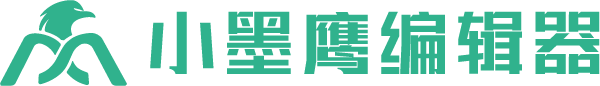我和乔坐在吧台前,不远处有人说话,音乐声不大。说话的是一男一女,不是情侣,举止很亲密。乔在等待,他的眉头隔一会儿就向上挑一下,这说明他在组织语言,等他们亲热完,至少是安静后,他大概有话要对我说。
他俩没让他等太久,又过了一首歌的时间,女人被男人的话逗乐了,男人对此感到满意,他们的肩膀碰在一起,女人把头靠在男人身上,交谈声停止了。
乔侧身面向我,邀请我喝一杯。
“不了,我开车来了。需要送你吗,一会儿?”我说。
“还是你那破车吗?没换一个?”他说。
“哈哈,经济条件不允许。”我笑着回复。
“别啊,”他把掉到前额的碎发向后拨,“我以为你写诗出书挺挣钱的。”
听完这话,我是真的笑了:“出书?我上次出书都是三年前了啊哈哈。唉,时间过得真快啊。”
他端起酒杯抿了一口,然后放下,用指腹刮杯沿上的水渍。
一男一女又开始交谈,这次声音比之前小,从女人的动作幅度看,他们快离开了。
乔快速瞟了他们一眼,然后问我有关两本诗集的事。
他说他之前有那两本书,可现在没了。
我知道他家有那两本书,是我送他的。
我如实回答他,其中一本已经绝版了,这是出版商的决定,我也无能为力。另一本还在售卖,市中心的书店就能买到,上周我去的时候,还看到了它,就躺在靠墙的大书架上,第几排来着……这个不记得了。
男女二人站起来,向大门走去,乔的眼神紧紧跟随他们,直到两人的身影消失在光线以外的黑暗里。他回头,意义不明地挑眉。
“怎么了吗?”我问。
“我要说件事,”他斩钉截铁,听起来像出走的一男一女给了他力量,“还记得三年前那次吗,那天晚上,我回家,看到你和我妹妹待在厨房里,然后我把你赶出去了,你差点连鞋都没穿上,就那次。”
“嗯……其实,你不用说得这么详细,我当然记得。”
那次,我的两本诗集刚出版不久,我想亲自给他送过去,但他不在家,我有意留下等他,就和他妹妹聊了会儿天,像普通朋友那样,全世界有无数和我们一样的人。
“那好,”他继续说,“你离开后,我把你送来的诗集扔了,就是这样。”
“这样啊……”
“我妹妹奋力阻拦我,跟我说你的好话,但这让我更生气了,你应该明白。”他又抿了口酒,灯泡就在我们头顶,光线沿着他的脸颊滑进酒杯,像一道瀑布。
“我只是写诗,”我轻声接过话题,“我不是文字的守护神,我不可能永远关照它们。就像神职人员,他们最多提供一个方案,或者一条路,至于信徒如何选择,不归他们管。我也是一样,我只负责写,不论读者如何对待我的作品,我都有权保持沉默。”
“不管怎样吧,”他看着我,“我想重新把它们买回来,在哪能办到?”
我注意到他一直在盯着我看,可能想正面目击我情感上的差池,以确定我的说辞不会改变。
我的说辞没有改变。
“《太阳之歌》,这本已经绝版了,出版商的决定。另一本,《包庇月光》,市中心的书店就有,余量可能不多了,要好好找找。”
正如我所说,我上次出版诗集是三年前,或者换个说法,我至少三年没出过一本诗集了。我的编辑联系我,按照合约,我上个月就该把最终稿交给他了,我表示遗憾,告诉他我会尽快的。
这是公开的秘密,而它不为人知的部分更加糟糕:事实上,我已经有八个月没连续写出两行诗了。 瓶颈期比想象中来得更早,我突然就有些走投无路。为了重拾创作,我试着把注意力从自我身上转移开,离开案台,走到房子外面,重新和朋友打交道,重新观察这个世界。
我暂时放弃了全职写作,到市中心应聘,成了一名书店管理员,每天穿着橙色的工作服穿梭于书架之间。当然,我没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。
偶尔,我能在书架的角落里发现我的诗集,它们基本都站着,也有的躺着,横躺在一些新书的头顶,挤压新书们的塑料封皮。我把手平着伸进去,取出诗集。那并不是书店提供的试阅本,但它的塑封皮已被褪去,书页有被翻阅和弯折的痕迹,有人读过它,至少摆弄过它。 我抬头,这里是“古典哲学”专区,我的现代诗集却躺在下面。我猜,它是被遗落在这儿的,故意遗落。它可能被人卷成一只鸟巢,夹在胳膊下,那人把手伸进口袋,拿出一便士,把硬币抛到空中,轻轻一抓,拍在手背上,再把手拿开,至此,卜卦已成,意为顺从,那人随手把诗集塞进书架,满脸轻松地走出书店。
想到这,我突然很庆幸自己没遇到“那个人”。
乔出现了,坦然穿过门口的一堆待整理书籍,走进现代诗专区,明显是要寻找什么。过了大概十分钟,他一无所获。就在这时,他突然发现书架上的书不止一层,而是并列的两层,他把小臂卡在书顶和书架架板的缝隙间,肩膀紧绷,不一会儿,两根手指夹出一本中等厚度的银灰色诗集。
《包庇月光》的试阅本。
我不知道那是不是世界上仅存的一本。
他翻开书页,从头开始阅读,前半部分读得很快,他的表情松懈,像在浏览一份早已检查过无数遍的财务报告,绝不可能有任何意想不到的内容出现。突然,他停下翻页的手指,视线在其中的某一页停留,我不知道那是哪一页,也不知道上面印着哪首诗,按照翻过书页的厚度推测,可能是《12月26日》,或者《上帝的驾驶证》,都不好说。
我更希望是《上帝的驾驶证》,虽然我说不清自己为何如此希望,可能因为那首诗的原型是他。
多年前的某个夏天,我开车带他兜风,那是他第一次坐我的车。开车前,他对我的车技表示担忧,反复把安全带的锁扣弹出来,再按回去。我试图让他放心,但可能是我不会安慰人,或者就是不会安慰他——这真的让我很苦恼——总之,开了几公里后,他强烈要求我停车,我只好答应他。他把我拽到一家酒吧里,不顾我的挣扎,硬是给我灌了半瓶威士忌,在确定我不胜酒力,不可能再开车后,他打电话给朋友。他的朋友开来一辆大拖车,我们坐在前面,我的车被挂上钩子,跟在后面拖着,像一头年幼的灰鲸,尚且不能独立生存,必须始终跟在妈妈身后。在车上,我试图和他说话,可他拒绝和我交流,把脸别过去,摇下车窗。车速界于快与慢之间,微风拂过车厢,吹起他的碎发。
是这样的,我能记住的就这些。我隐去名字,把他写进诗里,还发表出来了,印在一个全世界都有机会看到的地方,只要人们想。当然了,我没告诉他这件事。
乔笑了,笑得很突然,当我还在推测他翻看的页数时,他就那么毫无征兆地,突然笑了。他向后仰仰脖子,耸肩两次,右手的手指夹住书页,左手快速别过封面,眼睛盯住封面上的大字——包庇月光,看了很久。他重新回到那页诗,眼神在行距间跳跃,像公路警察,目击我的韵脚超速驶过。
他找到管理员,希望拿到一本全新的诗集,管理员帮他在门口附近寻找,我转身藏进高大的书架后面。
我捏了捏自己的喉咙,它摸起来像黏土,但紧张不安。平时我习惯用右手写字,现在我的右臂开始发痒。
我握着拳,像把一些黏土攥在手心里。我用手背抹了抹橙色工作服冰凉的外皮,然后轻轻掀起它,把黏土塞进我自己衣服的口袋里。
下班后,我要带着黏土回家,
用它们,捏成一个,故事,
或者,一首,诗,
反正,我有大把的,时间,
反正,我闲着,没事干。
(作者:沈好雨,2003年12月出生于黑龙江哈尔滨,性别女,汉族,现就读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)